| 猶太人:世界史的缺口,失落的三千年文明史──追尋之旅(西元前1000-1492) 一窺無國、無家的猶太人,如何在帝國與強勢文化的圍攻下,保有自己的價值。BBC名主持人西蒙•夏瑪耗時40年,書寫猶太人的歷史。西方權威主導的歷史,是基督徒的歷史,是想像的歷史。當訴說的角度與材料被宗教、政治力量左右;當人們聽見的聲音、閱讀的史書全被強權論述掌控,歷史便裂開大口,有了空缺。 猶太人的歷史就是缺口的歷史,在主流書籍裡,猶太人只有掌握金權、受迫害的那一面,但實際上他們在這世界上的角色比我們想像得都要深沉、重要。 ※ ※ ※
內文選摘(節錄)
追蹤摩西足跡的人雖然把自己看成是現代人,但像斯坦利,他們也同樣熱切希望把自己當作當年的以色列人及其領袖。斯坦利在一八五二年曾興奮地寫道:「毫無疑問地,我們走在以色列人當年走過的路上。」他認為,點綴在沙漠中的一叢叢多刺野生金合歡,就是《出埃及記》第三十章描寫會幕時提到的皂莢木(shittim,或什亭木),也肯定就是所謂的「火燒荊棘」。博學之人會保持清醒以免落入怪異傳說,然而在被認為是以色列人一度暫停,隨後又自此地出發的艾因穆撒,亞瑟.斯坦利卻全然沉迷於一種維多利亞時代獨有的聖經式浪漫。「今晚,我看到了落日後的星光乍現,也看到了一輪滿月,站在向遠處延伸的沙漠上,另一邊是深黑色大海的湧動和阿塔卡(Atakah)山頂閃動的銀光。」
在威爾遜軍備勘測隊中,愛德華.帕爾默算得上是一位古怪的抒情詩人,同時是一位貝都因民族誌學者,還是一位研究穆斯林流變和摩西史詩的專家。嚮導和修道士每天都對著那些西奈朝聖者和觀光客胡說八道,雖然帕爾默對這種此懷有一種善意的懷疑,但有時在深山中的要塞裡,他也會發思古之幽情,陷入思考:「無論怎麼看待這些傳說的真實性,都不能使我們擺脫心中的敬畏之情。」在拉蘇撒費(Ras Sufsafeh),他面對岩石表面的一道裂縫,完全把科學拋到了腦後,陷入了對「神跡」的思索,流露出一種拉斯金(Ruskin) 式的山水詩情懷:「多麼莊嚴而可畏的岩石,它彷彿平原上聳立起的巨大峭壁,輕蔑地擬視著地上的世界。說到見證古老律法,又有什麼東西能比這堆灰白的石頭更有資格?」突然間靈光乍現,他又接著說道:「摩西可能就在此僻靜之地與長老們分開,不需要多少想像力就能明白,『十誡』正是自這道岩石裂縫中頒布的……誰又能說,飢餓的以色列人不是在我們面前這片暗黑土地上受到誘惑而犯罪,吃下了獻給亡者的祭品呢?」 被他們稱作「神聖地理」(sacred geography)的樂觀主義,開始壓過科學調查的責任。當《西奈軍備堪輿全圖》(Ordnance Survey map of Sinai)於一八七○年以大開本、藍色封面出版時,《出埃及記》中的相關章節就標注在地名的上面。所以,拉哈平原(Raha)的上角標有「《出埃及記》19:12」,表示這是以色列人聚集的,真實的、「冒煙」的西奈(何烈)山前面的那塊地。帕爾默樂觀地宣稱,在沙漠綠洲中發現的一片石頭地基,肯定是當年以色列人營地的遺跡,其他人對此並無異議。對西奈進行勘測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於,這項工作將使「出埃及」這一事件,通過詹姆斯.麥唐諾的一幅幅照片,不僅在那些追尋以色列人足跡的人──考古學家、測量員和士兵──心中,而且在歐洲和美洲的廣大讀者心中,變得「真實」起來。 麥唐諾在照片拍攝過程中,面臨各種極端的困難:不僅要在熾熱的沙漠中製作濕火棉膠片,拍照時還要有足夠長的曝光時間,然後還要在帳篷裡把照片洗印出來。儘管如此,他還是變戲法似地,莊嚴呈現出了西奈山巒的形象,從而深深印在那些希望親眼目睹摩西曾經佇立,並從上帝手中接受「十誡」和律法書之處所的人腦海中。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幹什麼,他要在深深河谷和高聳的山峰之中,找出一個個上演過偉大史詩的小型圓形劇場。或許像愛德華.帕爾默一樣,這位上士內心升騰著一種絕對的信念。而毫無疑問,那些購買了這本令人震撼的攝影集(總計拍了三百多張照片,書中收錄一百張),或者說,進而感受到這些壯觀景象的人都會覺得,擺在他們眼前的,就是當年摩西創造一神教時的現場。 正是這些文字、形象、測量與地圖的完美融合,再現了這個故事的各個情節,雖然這個故事就形式而言只屬於以色列人,但在這些神聖的地理學家心中,其中的重要時刻卻是屬於全人類的。它們敘述的歷史清晰可聞。在遙遠的古代,一個受奴役的民族,由於祖先與耶和華立約而自異邦世界解放,從而獲得了新生。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事件發生於西元前十三世紀拉美西斯二世 統治時期,完成於出埃及的神顯。據《申命記》記載,摩西接受了《律法書》並將其作為他在尼波(Nebo)山去世之前傳給後世的遺產,《律法書》賦予了以色列人「有約在身」的獨特意義。接著,他們與善於征戰的約書亞一起進入迦南,最終創立了以耶路撒冷為中心的大衛王朝。在信奉多神的諸帝國中間,只崇拜一個獨一、無形的上帝,這令他們與眾不同。他們將這種獨特性用文字形式記錄在《聖經》中,具體制度化後凝聚在聖殿裡,經歷所有的塵世劫難。 用現代科學的語言傳播這些核心的真理,可以賦予《聖經》敘事更多的歷史真實性。那些最不可能發生的奇蹟,可以作為詩意的誇張而不予採信,但正如語言學家對某些《聖經》文本寫作的線索進行辨識和追溯一樣,十九世紀晚期的這一代人,對《聖經》真實歷史的重新發現是具有開拓精神的。這是《聖經》考古學誕生的重要時刻。教長斯坦利在巴勒斯坦地區探險基金會成立之初所期望的經驗證據(empirical vindication),後來成為一代又一代考古學家的畢生使命,從世紀之交的查爾斯.弗林德斯.皮雷(Charles Flinders Petrie),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傳教士的兒子奧伯萊(William Foxwell Albright),再到伊格爾.亞丁(Yigol Yadin)等眾多以色列「戰士」考古學家皆是。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儘管經過一個半世紀的不斷探索,卻沒有找到任何關於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從東部征服迦南之前在西奈曠野中流浪了四十天(比四十年要短得多)這段歷史的線索。在第十八王朝以後,埃及人唯一一次提到以色列人,是關於自己擊敗和驅散以色列人的戰事紀錄。後來,《聖經》研究的樂觀派指出,一切事出有因:埃及人怎麼可能會把他們自己軍隊被消滅的戰況紀錄在案呢? 在出埃及事件作為虛構的史詩被擱置起來之前,有個值得深思且難以避開的問題。學者們對於《希伯來聖經》中最早的古代文體的看法沒有爭議,而且有高度共識,比如〈紅海之歌〉和〈摩西之歌〉。這種文體與西元前十二世紀青銅時代晚期,近東地區其他相似的古體「詩歌」文學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果他們是對的,在文體上,〈紅海之歌〉與腓尼基人的風暴神巴力征服大海的史詩有許多相似之處,那麼為什麼早期的以色列詩人在上述事件發生僅一個世紀後,卻創作出了如此具有自身特點的史詩呢?若非有什麼故事留存在民間的記憶中,那麼為什麼其中那些受奴役和被解放的可歌可泣情節,會完全不同於其他原型呢?有一種極端懷疑論的觀點,甚至虛構出一個當地的迦南人分支;他們居住在猶大山區,通過一段神秘的分裂、遷徙與征服的歷史,使之全然不同於其他迦南部落和城邦,且還至做了特別詳細的地形圖加以佐證。究竟為什麼會生出這樣的故事呢? 此即我們講述猶太人的真實故事時所處的背景。除了《希伯來聖經》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證據,可以證明出埃及和接受《律法書》的歷史真實性。但這並不一定就意味著故事的某些情節沒發生過,例如:賣身為奴、長途跋涉,甚至後來重占迦南。因為正如我們所見,僅僅是希西家水道的發現,就足以證明《聖經》故事的某些篇章,毫無疑問地為真。 當然,我們不能在沒有證據,或只有反面證據的情況下憑空構建歷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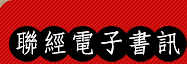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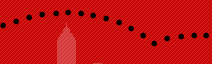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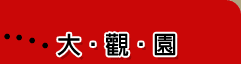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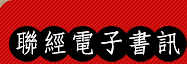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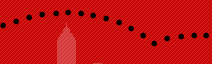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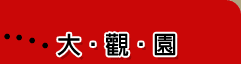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