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Ⅰ
從梁實秋的散文譜系與時代意義、林語堂的歷史定位、余光中的散文實驗、余秋雨對歷史文本的影像化、莫言的暴露與雄辯、董橋在帝國餘輝裡的拾荒、楊牧的無盡搜尋、三毛的分裂敘事主體、簡媜對美的追尋,民間的集體飢餓記憶、旅行中的書寫,到美食在散文的出沒方式。 鍾怡雯在《雄辯風景:當代散文論Ⅰ》一書裡,論述範圍涵蓋了九位重量級散文大家,以及三個影響深遠的散文創作浪潮,由此建構出當代散文在美學和議題上的變革。 二、舌頭的記憶 原料須加工之後方成美饌,相同的菜色到了不同的廚師手上,它會呈現不同的口感。飲食如果在散文中是原料,那麼飲食散文就是作者加工之後呈現於讀者的菜餚。(作者)烹調功夫的高下,決定了(散文)佳餚的美味/精采與否。因此同樣是寫米線,它在唐魯孫的筆下是一種單一的敘述,作者交代它的來源,並用很大的篇幅來敘述米線的傳說,至於它的滋味,讀者大約知道是「甘肥適口熱氣騰騰的美味」。可是在趙繼康的筆下,米線卻帶著歷史的情感和懷舊的滋味: 受盡「文革」千古浩劫和磨難的老百姓,嬉笑顏開地吃上了「小鍋米線」,既是家破人亡或焦慮經年身心疲憊的少許生活安慰,也是具體感受到鬆馳了階級鬥爭那根繃得過緊的絃。 米線本來是雲南的一種地方食物,但是經過了歷史的浩劫,它成了一種集體記憶。一碗加上酸菜和「甜皎頭」(類似大蒜頭)的米線,那混合著酸、甜、辣的小吃,是安定生活的滋味。米線在四人幫瓦解之後的再現,不但是後毛澤東政權的一種象徵,也是即將對外開放旅遊業的先兆。它意味著階級鬥爭已經成為歷史,老百姓隱約看到了生活的曙光。 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美食是一種感官的享受,是物質性的;可是當它以文學(散文)的方式出現,它必須「轉化」原來的物質性,依附抽象的表現方式而存在,因此任何食物都必須經由符徵演繹到符旨的過程,才可能轉化,才可能生產意義。所以同樣是寫魚翅,林文月是藉以懷人,梁實秋則以魚翅為焦點,把他對魚翅的「知識」逐一陳列─包括不同地方的魚翅特色、作法和價格等;而唐魯孫則是介紹北平不同飯館的魚翅之別。 林文月在〈潮州魚翅〉中不厭其煩地詳述她烹煮魚翅的細節,從選翅、發翅到烹煮的心得和祕訣,其繁瑣細碎,步步為營而又耗時耗力的做法,她自稱為「藝術之經營」。既是藝術之經營,則必得吸取前人的經驗,同時亦須有自己的發明,此所以烹飪和藝術相似之處。因此《飲膳札記》十九篇之數,上承〈古詩十九首〉,而所書之內容大異。〈潮州魚翅〉的烹調方法既前有所承,亦有主廚者的獨特慧心,因此閱讀〈潮州魚翅〉就宛如品嘗一碗做工費時,滋味極美的「潮州魚翅」。那碗潮州魚翅的滋味,實添加了懷人憶舊的滋味。 《飲膳札記》共有十九篇,目錄和《雅舍談吃》一樣,乍看之下都是菜餚。作者宣稱本為免遺忘其製作過程而寫,記事為次;然而在讀者的閱讀經驗中,這些伴隨菜餚而生,對人事的記憶才是彌足珍貴的,正如書中附錄林文月對《杜鎮艷陽下》一書的評語:
梅耶寫食譜,其實未必是機械式單調的筆法。筆尖不小心常會開溜,去回憶好的母親或是幼時在家幫傭的一個廚子。食譜的滋味,遂往往味在舌尖而意在言外了。 這「筆尖不小心常會開溜」,「味在舌尖而意在言外」,才是飲食散文的價值所在。因此《飲膳札記》貫常見到對親人和長輩的記憶,譬如寫魚翅而有老師臺靜農對魚翅「柔軟之中又保留一點咬勁」的標準;父親鍾愛這道美食,食畢不留一絲餘羹;以及記述師長於宴飲之際的歡樂氣氛,真正達到了「飲食,所以合歡」的境界。是以在〈紅燒蹄參〉中,一個燒糊的紅燒蹄膀,竟在酒興與談興正濃的聚會裡,成了記憶中最美好的一味,反而其他精心燒製的佳餚,在時日漸久之後,都逐漸被遺忘了。因而紅燒蹄膀不但成了歡樂的象徵,吃時「往時朋友們談笑爭食油亮蹄膀的皮而嘖嘖歎賞的情景,也每常歷歷如在眼前」。如今有的老師已逝世,有的深居簡出,不再參與飲宴之事,令那道菜餚產生一股悲欣交集的滋味。 「佛跳牆」是一道匯集眾多山珍海味的葷食,這也是融合最多人事回憶的菜色。林文月孩提時聽母親傳述外祖父的往事,無意間聽到這個令人好奇的菜名,知道寫畢《台灣通史》的外祖父曾居住於大稻埕,常與騷人墨客飲宴於其間,最愛的佳餚即「佛跳牆」,而後家裡一位資深的師傅「吉師」亦擅長此道,常於假日全家相聚於北投洗溫泉時,烹煮這道菜。難怪林文月覺得雖然日後在別的場合吃過同樣的菜,「但似乎皆不及少女時代與家人同嘗過的吉師的手藝高妙」,於是嘗試動手製作,整個詳細的烹調記錄實是回憶的過程。 林文月的敘事節奏淡定舒緩,烹煮的細節交代幾近求完美,譬如這樣的段落: 將瓷甕放置入蒸鍋中央部位,徐徐注入清水;水無需太多,多則往往令甕浮動不穩,故以淹過甕肚約五、六分高之量為宜。甕本身之重量,加上蒸鍋之內已注入相當多的水,至此全體總量更為沉重,所以不妨將蒸鍋事先安置於爐上,省免搬運之勞。爐火先須旺,等水開沸之後,可以轉弱,維持蒸鍋內之水繼續滾騰即可。這時候,鋁製的鍋蓋可能因水氣不斷沖頂而浮震擾耳,可用一小而有重量之物(例如磨刀石)平置於鍋蓋之上鎮壓之,既可防止擾耳之聲,又有助於減少水氣過分外散。 這段文字是烹煮之前的預備動作,簡單的說,是「所需的水量約至甕肚五、六分高」,但是林文月演繹這個動作,卻用了二百多字交代需要留意的事項,詳述「必得如此」的道理和緣由,如此不厭其詳的提示和記錄,其實是在召喚記憶中那鍋已經不可能再出現的佛跳牆,就好像平時拘謹而不苟言笑的舅舅吃到她做的芋泥,不免也想起母親和姊姊,而變得親和起來;一枚晶瑩剔透的水晶滷蛋,可以令人想起一個教授露出幾近頑童的表情,都是記憶的力量在作用,它使一道食物上升到精神的層次了。《飲膳札記》原來的初稿是作者於宴客時所做的筆記,記錄菜單、宴客的日期和客人的名字,原來只為實用的目的,她在〈跋〉裡這麼說: 但是重覽那些陳舊了的記錄文字,於一道道菜餚之間,令我憶起往日俎上灶前的割烹經驗,而那些隨意寫下的名字,許多年後再看,竟也有一些人事變化,則又不免引發深沉的感慨與感傷! 由此可見烹飪和記憶之不能分割,林文月於飲食的部分詳盡而於人事往往只是蜻蜓點水,那寥寥幾筆卻是文章的精魄,文章遂有了記憶的深度和時間的鑿痕,增添王勃〈藤王閣序〉所謂「勝地不常,盛筵難再。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于偉餞……一言均賦,四韻俱成」,那種宴終人散的唏噓! 相較於林文月那種盛筵難再的感慨,徐世怡則是透過飲食書寫回顧一個現代女性的成長,她認為「飲食文化是一群人在時空環境中,慢慢釀出花朵。打開生命的大鍋,回憶的味道總會裊裊溢出」。因此《流浪者的廚房》記錄的對象有食物,也有人物,是一個「飄泊者」為安慰自己的臟腑而烹調時,不經意挖掘出和食物不可或忘的成長記憶。「飄泊者」的意義有二:二十世紀末,越來越多的旅行者在旅路上度日,他們離家的理由雖然不同,想家時總不免想嘗一嘗家鄉的食物以緩鄉愁─這是在空間上的飄泊者。其次,是指那些想藉食物重溫舊夢,所謂時間上的飄泊者。這本散文集有很多食物是徐世怡留學比利時的記憶,許多時候做菜並不是為了吃,只是想化解鄉愁: 廚房裡裡外外忙忙碌碌的切啊剁啊,被解到愁的根本不是那些管「吃」的器官,比較實際的是,廚房裡裡外外的勞動已讓人無暇去孵愁鬱的蛋。器官們根本不懂事,它們只知道餓,只知道吃。 這裡徐世怡把精神和感官一分為二,飢餓的器官被餵飽了,可是精神上還是餓的,因此做菜變成是一種永無止盡的追尋,鄉愁是延宕的符旨,既然無法被把握,就無法去化解。所以她對烹飪的態度很隨興,也很任性,既不講究材料,也不重視正統口味,為的是烹飪過程中,那種從忘鄉晉升到忘我的快樂。 因此流浪者/飄泊者沉浸於烹飪遊戲的快樂,並不在乎烹飪的「技」如何。她專注於烹飪自身,如果按照詮釋學所說的,一切遊戲活動都是一種被遊戲的過程(alles Spielen ist ein Gespieltwerden),那麼烹飪的魅力,烹飪所表現的迷惑力,對於徐世怡來說,正在於它超越烹飪者而成為主宰,她並不在意求烹飪的結果如何成功,而是充分玩味烹飪,就像庖丁解牛時忘了牛的存在,而進入一種藝術的忘我境界,也即伽達瑪所說的遊戲狀態。 學會包水餃和做包子之後,徐世怡形容自己「像瘋了一樣迷上這種『展現手指功夫』的手工藝」,因為那是表現拿捏手工的遊戲。包水餃要達到餃子可以壯麗地站立才算好玩,因此要有點幾何學的直覺的功夫,她認為那是一種「手工幾何」:「包水餃過程中的每一個捏合就是在創造點面的接合點,這整張軟軟的麵皮被我的手指拉塑出包容性的幾何函數」。她其實是想藉包餃子時,再浸潤於兒時「爸爸揉麵粉,小孩在旁玩」的時光。父親認真揉麵粉的樣子,空氣中那股充滿麵粉發酵的香味,就是「幸福」的味道。因此廚房往事永遠離不開人間煙火,食物必須沾染人的氣息,才能讓人記憶。水餃的意義對徐世怡而言是十分繁複的,那也讓她想起二姐,二姐包的水餃,以及她慘淡的青春期。作者用了一大段文字挖掘記憶中的水餃天鵝: 她就是可以把水餃包得挺傲有角。和別人的水餃比起來,她的水餃隊伍簡直是一排巍巍站立的天鵝湖芭蕾舞群。水餃從腰窩孤度拔起挺胸的曲線,我幾乎要懷疑那些驕傲的水餃已經長出脊椎骨了。軟軟的一張圓皮被拉成連續的幾何平面,薄薄的皮裡包著結實的肉餡,伶俐的彎皮角度下藏著不破皮的韌度,二姐捏出的水餃就是與我們這等泛泛之輩有很大的不同。她的每隻天鵝都挺胸揚顎,整齊白淨,那麼整齊的角度活像訓練多年的古典芭蕾舞團。 作者把二姐所包的餃子比喻成優雅美麗的天鵝,整個敘述視角都扣緊天鵝的意象而鋪陳,水餃挺立的姿態是天鵝湖芭蕾舞群,從天鵝而轉到天鵝湖芭蕾舞群,水餃的比喻換了兩次,為的是更形象化水餃栩栩如生的形狀,繼而以擬人化的修辭「驕傲」加強讀者對水餃的敘述,也強調二姐所捏的水餃和她的有多麼不同。那挺胸揚顎,整齊白淨的天鵝實有雙重意義:第一重是指二姐就像她所捏的水餃天鵝,當時已亭亭玉立,而自已則是暗中崇拜她的醜小鴨;第二重意義指涉那些美麗的天鵝是「童」話,只合存在「故」事裡。因此二十年後,當已有兩個小孩的二姐茫然的搖頭,表示早已忘了怎麼包水餃時,徐世怡不由得惋嘆「人會長大,天鵝也會老、會死;時光的湖水往前流,還有誰是什麼都記得呢?」 徐世怡的飲食散文和林文月最大的不同之處在於,林文月幾乎通篇敘述菜餚的製作方式,對人事往往輕輕幾筆掠過;徐世怡則是著重依附食物而生的事件,食物是草蛇灰線,帶出五味雜陳的記憶。譬如吃飯這件事,在徐世怡的童年記憶中,是小孩「吃飯看電視」,而爸爸「吃飯配報紙」。至於蛋糕食譜,則令她想起留學時,那個富裕而憂鬱的台灣女孩。那女孩的憂鬱來自於對未來的迷茫,她順著父母的意思去留學,但對未來十分徬徨,到比利時既不是為了唸書,也不是工作,更不想嫁人,她年輕又漂亮,穿最好的衣服,「但她駝著背
的身體卻包住一種對什麼都提不起勁來的老味」,就像少女做的蛋糕「鬆鬆軟軟」的,而少女是「散散茫茫」的,是一個失血的生命。因此她從少女那裡拿了蛋糕食譜,卻經過大力改良,似乎潛意識裡抗拒像少女那樣,只有等待的生命模式。 梁實秋所寫的〈芙蓉雞片〉一文,懷念的是北平的東興樓館子,當年一起在此歡聚的友人,以及父親的教誨。幼時隨父親到東興樓,他因不耐上菜稍慢,而以牙箸敲盤碗,這樣的一件小事,卻有著許多人情世故在內: 我用牙箸在盤碗的沿上輕輕叮噹兩響,先君急止我曰:「千萬不可敲盤碗作響,這是外鄉客粗魯的表現。你可以高聲喊人,但是敲盤碗表示你要掀桌子。在這裡,若是被櫃上聽到,就會立刻有人出面賠不是,而且那位當值的跑堂就要捲鋪蓋,真個的捲鋪蓋,有人把門簾高高掀起,讓你親見那個跑堂扛著鋪蓋兒從你門前急馳而過。不過這是表演性質,等一下他會從後門又轉回來的。 不過是敲盤碗這樣的小動作,這在歷史悠久,重視飲食文化的飯館,卻可以詮釋成是要「掀桌子」。這意味著吃飯不僅是攝食的生理活動和物質活動,也是心理和精神活動,正所謂吃飯皇帝大,當用餐的情趣受到破壞,譬如菜上慢了令客人不耐,飯館要求當值的跑堂捲鋪蓋,是表示極為重視客人必須在愉悅的情緒下用餐,為平伏客人的不滿而做的假動作。但這偶然的疏忽並不至於要讓人失掉工作,所以是「表演性質」,讓他兜個圈又從後門轉回來,只要達到提醒的作用即可,從這裡我們也看到人情之厚,一個有飲食文化的民族處事之迂迴。 《雅舍談吃》多次提起父母。譬如寫〈鍋燒雞〉一文,雖是記一種下酒的菜餚,在梁實秋的記憶裡,它勾起的是一個六歲男童的醉酒記憶: 第一個房間是我隨侍先君經常占用的一間,窗戶外面有一棵不知名的大樹遮掩,樹葉很大,風也蕭蕭,無風也蕭蕭,很有情調。我第一次吃醉酒就是在這個房間裡。幾盃花雕下肚後還索酒吃,先君不許,我站在凳子上陷舀起一大杓湯潑將過去,潑濺在先君的兩截衫上,隨後我即暈倒,醒來發現已在家裡。這一件事我記憶甚清,時年六歲。 這段文字的可觀之處,在於它體現了飲食文化中重視宴飲環境的傳統。六朝時阮籍等七賢聚飲嘯歌的竹林,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的「花間」;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具美的王勃會飲之滕王閣;歐陽修筆下環山臨泉,翼然而立的醉翁亭,是集天工、人工,內、外、大、小於一體的絕妙環境。袁宏道對宴飲環境有所謂「醉花」、「醉雪」、「醉樓」、「醉水」、「醉月」、「醉山」之說,而梁實秋筆下那棵濃密的大樹,亦製造了一個非常詩意的用餐情境,那樣的情調也許讓一個小孩模模糊糊的感受到美的薰陶,加上大量酒精的作用,於是便演出一場那樣澆一大杓湯到父親身上的醉酒鬧劇。或是在酒席吃到不對味的涼拌海參時,特別想念父親那獨特的配方,於是〈海參〉一文中那一段涼拌海參的敘述,實為懷念父親之思。 於〈筍〉一文詳述各種筍的掌故之餘,不能忘記的是母親的冬筍炒肉絲:「我從小最愛吃的一道菜,就是冬筍炒肉絲,加一點韭黃木耳,臨起鍋澆一杓紹興酒,認為那是無上妙品─但是一定要我母親親自掌杓」。這樣由母親掌廚的冬筍炒肉絲,除了是廚藝之巧外,尚有母愛的味道。或是吃遍天下的炸丸子,卻最不能忘記七十多年前,母親特別為嘴饞的小孩叫來的那碟同和館的小炸丸子。也許那碟炸丸子並不特別,而是時間的距離和對母親的記憶,使食物變得可口。無論是鍋燒雞、海參、冬筍炒肉絲或是炸丸子,這些「食物」皆因攀附著親人的記憶,轉化成再也難現的「美食」。 在唐魯孫為數眾多的飲食散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北平、上海、台灣的包子〉。 除了圍繞著包子的焦點敘述之外,他把敘事延伸到「人」的層次,在記述北平「河間包子」時,描寫一個做包子的師傅,人物的形象頗能和包子的外形綰連: 筆者當年每天中午在潤明樓吃飯,憑欄下顧,就看見一個胖子在一座白布蓬裡一邊包一邊蒸,忙得井井有條,胖子胖得眉眼都擠在一起,永遠笑咪咪的,跟當今影劇雙棲藝人葛小寶彷彿兄弟一樣,兩隻手揉麵活似兩隻大肉包子在那裡翻動,尤其到了夏天,他穿一件夏布小坎肩,胖嘟嘟的身材渾身哆哩哆嗦,時常引得路人駐足而觀,他做的包子別具一格,既沒滷汁更沒湯水,餡子鬆散可是柔潤,同時保證不摻味之素,他的緊鄰就是爆肚王,叫一碗水爆肚配合著河間包子吃,凡是吃過的主兒準能回味出當年那分滋味吧! 這個包子師傅福態的外貌十分有喜劇感,很能搭配包子的形象,作者說他「兩隻手揉麵活似兩隻大肉包子在那裡翻動」,幹起活來渾身都抖動,這樣的「肉」感很容易讓人把他和「肉包子」貫聯在一起,當作者憶當年的時候,立刻勾勒出那副令人難忘的市井圖─包子師傅和路人、包子加上水爆肚,形成兩條糾纏的記憶線路,那不只是味覺的,同時也是鄉愁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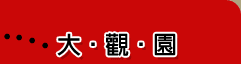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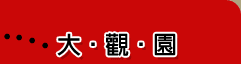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