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
作者:顏崑陽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任輔仁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兼擅學術研究與文學創作:學術博及中國古典美學、文學理論、老莊思想、李商隱詩、蘇辛詞、一般詩詞學、現代文學批評等。著有:《莊子藝術精神析論》、《李商隱詩箋釋方法論》、《反思批判與轉向》、《詮釋的多向視域》、《詩比興系論》等十餘種。創作以古典詩詞、現代散文、小說為主,曾獲聯合報短篇小說獎、中國時報散文獎、中興文藝獎章古典詩獎,著有:《顏崑陽古典詩集》,短篇小說集《龍欣之死》,現代散文集《窺夢人》等十餘種。
※ ※ ※
21世紀的中國人文學術,
必須突破「五四」時期所建構且已僵固的
「舊知識型」的「圍城」,
才能開展真正現代化、當代化的「新知識型」,
形成「典範遷移」。
顏崑陽精銳的反思、批判「五四知識型」,揭明其迷蔽,提出除迷解蔽之方;從人文知識之本質論與方法論的根本處,詮釋視域應該如何轉向,破而能立。對於個別論題如「五四」以降,被淺識的學者們曲解到不成形、貶責到一文不值的〈詩大序〉問題;被矇眼的文學史作者們誣衊為抄襲的漢代「擬騷」問題;被腦袋僵固的學者們將「實用性」與「藝術性」一刀兩斷的文體、文類問題等,這些「五四知識型」之迷蔽而不識其真理的問題,《學術突圍: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突破「五四知識型」的圍城》書中都逐一滌塵刮垢,揭明要義;意圖呼喚學界,共同完成中國現當代人文學術的「爆破」與「重構」工程。
※ ※ ※
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現代」?如何「當代」?
一、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現代」?如何「當代」?而學術「典範」(paradigm)又如何能形成遷移?
這一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主題是:「文學研究的當代新視域」。三個子題是:(一)傳統文學轉換出當代新的詮釋視域;(二)當代社會文化(與文學)所開拓的新議題;(三)當代引介西方理論所開拓的新詮釋。這個主題以及三個子題,隱示著「當代」中國人文學術在繼受「五四」這一知識年代所開啟的「現代化」視域之後,又意圖轉進到另一知識年代,而開啟「當代化」的新視域。這會是當代人文學者對中國人文學術「典範遷移」的呼喚嗎?即此,我想追問的是:中國人文學術如何「現代」?如何「當代」?而「五四」時期所建構的學術「典範」(paradigm),到二十一世紀的當代,又如何能形成遷移?
典範(paradigm)這個概念,自從孔恩(T. Kuhn,一九二二─一九九六)《科學革命的結構》傳播到台灣 ,就經常被應用於人文學術的論述。它指的是學術社群所共同承認一套經由完善的研究成果而建構的知識體系,以此作為「常態科學」研究的基礎,人文科學也可包括在內。
一種學術典範,包含下列幾個構成要素:第一是所研究之知識對象「本體」的界定,從而建構一種特定的「本體論」;第二是由此所生產之知識「本質」的界定,從而建構一種特定的知識「本質論」;第三是提出若干基本問題,從而解答這些問題,以建構必要的基礎知識,包括某些命題、理論或模型。第四是一套適當而可操作的方法,這套方法包括原理、原則及實際操作的技術。
「典範遷移」,從來都不是一種「知識型」(Épistème) 之枝枝葉葉的改變,當然就不只是某些陳陳相因之舊議題局部的修補;而是從「根本」處轉換創新的詮釋視域。
「人文知識」不是上帝創造的現成物,而是人類創造的文化產品,並無超越經驗事實而先驗存在之絕對、普遍、唯一的「本質」。任何一種人文知識的「本質論」,都是某地區、某民族、某歷史時期的某人文學家,在文化傳統與當代社會的實存情境中,所作「規創性」的定義。而任何定義也都非固著不變,即使同一區域、同一民族,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學者,都可以針對某一種人文知識的「本質」作出重新的定義,提出一家之言的理論,而付諸實踐,由應然的定義經由實踐而創造實然的產品。
因此,「典範遷移」乃是一代「知識型」的革命,必須從研究對象的「本體論」及其知識「本質論」與相應的「方法論」,提出革命性的新定義,以重構一套殊異於前一個歷史時期的知識型。不過,前後不同知識型的遷移,並非截然為二,其間仍存在「因/變」的關係。
中國人文學術的現代化、當代化,以至「典範遷移」,如何可能?「務本」之道就是經由對「五四知識型」全面而深切地反思、批判,進而重新定義研究對象的本體論、知識本質論與方法論,並付諸實踐。
二、何謂中國人文學術的「現代化」與「當代化」?
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展開於晚清,至今已經歷了漫長過程。中國晚清以降,追求「現代化」的風潮,預設了改變對立面之古代傳統社會文化的革命性意圖,甚至一度強烈到非理性地高喊丟棄一切社會文化傳統。
西方一般所謂「現代化」,比較偏向指涉十八世紀以降,由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所帶動科技與經濟生產方式的改良,顯現在表層的物質文明,主要是生活工具、醫療、運輸、資訊傳播等方面的進步。雖然,廣義的「現代化」涵蓋了十八世紀以來,總體社會發展的過程;但是,經常被片面突顯的還是「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過程,「科技」的工具製造與「經濟」的價值生產是關懷的焦點。
中國晚清以降,新知識分子追求「現代化」,其側重面就是在於「物質文明」;跟隨西方社會工業化的趨勢,追求科技、經濟的現代化生產,以達到船堅砲利,富國強兵,這是短視之士主要的改革目標。
至於在「精神文明」方面,通常使用「現代性」(modernity)這一概念。晚近西方有關「現代性」的論述,乃是用來解釋自十八世紀文化思想的啟蒙運動、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直到二十世紀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整個歐洲的文化價值觀、社會倫理、政治制度、經濟生產關係,長期演變的主要性徵及趨勢。其關注的焦點是這種性徵與趨勢的「理性化」過程,因此是比較深層之思想的變遷,尤其是科學精神、社會進步、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尊重個別差異等觀念的秉持與實踐。
準此,則「現代化」與「現代性」的思潮及社會文化發展進程雖有密切關係;但是,二者的涵義原不等同,卻經常被混用。中國晚清以降,一些很有思想高度的新知識分子,例如嚴復、梁啟超、胡適等,他們所倡導、論述之文化、學術的「現代化」,科學、民主與自由是重點。因此,他們所說的「現代化」,其實也混合著「現代性」的概念。至於台灣學界,有關文化或文學研究,「現代性」一詞幾乎已是到處氾濫的口頭禪;但是,「現代性」的基本概念,很多論者自己也說不清楚。
我們在這裡雖然辨析了「現代化」與「現代性」涵義的差別;但是,順隨晚清以降,嚴復、梁啟超、胡適等新知識分子倡導、論述「現代化」的歷史語境,他們所說的「現代化」其實偏重在追求文化、學術能從傳統的窠臼掙脫出來,邁向西方式的精神文明;而不是特別指涉「科技」與「經濟」生產的進步方式。
因此,我們在這裡使用「現代化」一詞,沿著這樣的歷史語境,就讓它也混合著「現代性」的概念,偏指文化、學術能從傳統創變出來,而開拓現代的詮釋新視域。但是,「反傳統」卻不再是我們固著的「文化意識形態」;相反的,在「後五四」時期,我們認為中國文化、學術的「現代化」,更必須回歸傳統而重新正確、深入地理解傳統;學者們應能自覺地朗現民族文化主體性,而在承繼傳統的基礎上,創變出具有民族性以及時代存在經驗與詮釋視域的文化、學術產品。
相對於古典傳統文化,晚清以降,「現代化」有其漫長歷程,當然也有階段性的變遷。我們所面對當前的時代情境,已不同於晚清民初以及「五四」時期,梁啟超、胡適諸君子所面對的時代情境,這是「歷史時期」的差異性。同時,由於不同區域的人們對古代與現代文化接受的層面有別,社會關係結構與互動實踐方式有異,因此「現代化」也有其「區域空間」的差異性。那麼,台灣經驗的「當代」、大陸經驗的「當代」,以及其他域外漢學地區,例如日本、韓國等,他們的「當代」也都各有差異。
大體而言,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相對於古典傳統,「現代化」是所有學者身處的「共同情境」;而「當代化」,則是不同「歷史時期」與「社會區域」的學者各自身處的「差異情境」。在共對「現代化」的潮流中,每個不同「歷史時期」與「社會區域」的人文學者,都必須反身回顧自身的「當代」存在情境,以自覺的當代「歷史性主體」追問中國人文學術「現代化」,甚至「當代化」如何可能?例如,台灣現代人文學術的「當代化」,必須滲透二十一世紀這一「歷史時期」與台灣這一「社會區域」特有的存在經驗,而展現其他不同「歷史時期」與「社會區域」之存在經驗的「差異性」,這樣才稱得上「當代化」。人文學術必須「與時俱化」,並且「隨地共變」,才能表現貼切於學者之存在情境的特殊創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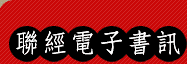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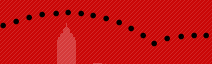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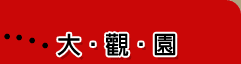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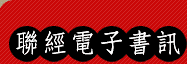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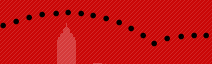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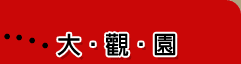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