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
卜正民繼《維梅爾的帽子》另一全球史力作
一幅被遺忘近350年的中國航海圖
連結17世紀中國的海洋帝國及全球大航海時代 了解「亞洲火藥庫」南海主權爭議的歷史起源
從域外、從海洋,更從全球視野看中國 【塞爾登地圖的祕密(節錄)】 班.瓊森有著永不枯竭的創造力、無休無止的野心和始終羞澀的阮囊,靠著揚棄嚴肅性質的論述,轉攻吸引目光的創作,聲名達到顛峰。他為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廷臣編寫假面劇劇本,得到豐富酬勞,1620年,他不負眾望推出另一部光怪陸離的劇作。《從月球上所發現的新世界傳來的消息》(News from the New World Discovered in the Moon)一劇,情節薄弱,美其名為劇作,其實幾可說是拿大量歌舞來娛樂這位我行我素的國王。但仍要有故事才能引起廷臣興趣,於是瓊森讓兩位傳令官在開演之初上台宣布:奇哉怪哉!月球人就要來英格蘭了。 在舞台上展現來自海外的外地人,給了瓊森一個選擇。他可以把他們打造為充滿異國風的人物,甚至野蠻人,而美洲人正可為他打造此類人提供參考。或者他也可以把他們打造成像他的觀眾那般文明有禮的外國人,儘管可能仍有一丁點差異。例如可以打造成中國人:中國人一向文明有禮。這齣假面劇中的舞者來自月球,因此瓊森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來打造。他選擇讓他們以文明人形象現身。兩位傳令官宣布,月球「新近發現是個有人居住的地方,有可通舟楫的河海、多種國家、政策、法律」;換句話說,和歐洲一樣,但他們又說「不同於我們」。差異很重要,或者更貼切的說,差異的程度很重要。若是完全一樣,即將現身的月球舞蹈團將完全不具異國風味。要讓看戲者興奮,小小差異不可或缺;至少他們的戲服應該稀奇古怪,或許他們的語言也應該讓人聽不懂。但如果要完全不同,月球人將得把觀眾心中那股受威脅的感覺演出來,營造出大不相同的戲劇氛圍:比較像打仗而不像喜劇。 八年前的1612年,威廉.莎士比亞在英格蘭國王和朝臣面前將《暴風雨》搬上舞台時,以不同手法處理充滿張力的異文化相遇情景。不是文明月球人來到文明開化的英格蘭,而是文明的歐洲人來到一座野蠻荒島。其中一個人物,以「不適人居且幾乎無法進入」之語形容他所看到的周遭環境。瓊森筆下的月球所具有的「國家、政策、法律」,在這座島上付諸闕如。島上只有一個土生土長的居民凱列班(Caliban),「一個渾身斑痣的妖婦賤種,無緣具有人形。」劇中主角米蘭公爵普洛斯彼羅(Prospero)被弟弟奪去爵位,趕出米蘭,最後流落這座荒島。凱列班則淪為普洛斯彼羅的奴隸。莎士比亞把凱列班打造為令人痛恨的粗暴之徒,但還是讓他講述自己的生平:他原是單純天真之人,初遇普洛斯彼羅時,毫無機心,張開雙臂歡迎他。正是普洛斯彼羅侵占此島之舉,創造出殖民惡行,才使凱列班變成後來那個樣子。凱列班如此憶及他粗暴的主人, 你教我講話;我從中的獲益
就只是知道怎樣罵人。但願血瘟病要了你的命,
因為你教我說你的那種話! 就連凱列班所祈求降臨於普洛斯彼羅身上的瘟疫,都是歐洲人入侵這塊無主之地所致,疾病使樂園黯然失色。在下一幕中,莎士比亞簡單描述了宣稱此島為無主之地後可能發生的兩種情況。他透過老顧問龔薩羅(Gonzalo)之口,講述了理想化的遠景。龔薩羅想像在這座荒島上打造完美的「共和國」:一個沒有商業或國家、合同或私人所有權、勞動或戰爭的體制。結果,與他一同遭遇船難的其他廷臣不留情面地嘲笑他是個老蠢蛋,把他的美好想像一百八十度翻轉,宣稱他的美好黃金時代將只會是個「充斥妓女與惡棍」的社會,龔薩羅最終將自封為那個社會的國王。他們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人世:置身自然狀態的人會追逐自己的私利,而這當然就是自這些廷臣為了自己的利益罷黜普洛斯彼羅以來,他們一直在做的事─且觀眾對此知之甚明。我們可以欽佩龔薩羅的真誠,但我們也非常清楚無主之地不可能有好的結局,即使專制君主是個仁君亦然。這齣戲以文明戰勝野蠻畫下含糊的結局:普洛斯彼羅失散的女兒米蘭妲發現自己最終置身於她的文明同類之間時,興奮大喊, 神奇啊!
這裡有多少好看的人!
人類是多麼美麗!啊,新奇的世界,
有這麼出色的人物! 《暴風雨》是莎士比亞的偉大劇作之一,《新世界傳來的消息》在班.瓊森的所有作品裡則永遠稱不上一流之作,但瓊森本就無意撰寫發人深省的嚴肅劇作。我在本書最後一章的開頭搬出這兩部作品,是因為它們讓我們見識到歐洲人與更大的世界相遇時處理手法的兩個極端,不管是如約翰.薩里斯那樣從船甲板上處理此一相遇(《暴風雨》演出時他正在航往萬丹的路上),或是如約翰.塞爾登那樣從手抄本的頁面上處理此一相遇(那一年他正為通過律師考試在準備)。《暴風雨》把新奇的世界看成一個迴異的地方,一塊要人順服或流亡的蠻荒之地。《新世界傳來的消息》在陌生異域裡尋找熟悉之處,承認異地的法律和習俗可能不同於我們的法律和習俗,卻不會威脅到我們。薩里斯和塞爾登採取瓊森的作法。世上的國家和民族各不相同,但在本質上卻無二致。薩里斯可不必動武征服就能和他們通商,塞爾登可鑽研他們的文獻,尋找開明之人的共同本源。要再過一個世紀,這一平等對待意識才讓位給高高在上的心態,那時英國東印度公司才開始把重心放在奪取世界的資產和其他民族的尊嚴上。 瓊森和莎士比亞殊途同歸,給了英格蘭觀眾所心儀的東西:對英格蘭本土之外的遙遠新世界的想像。他們這麼做時,只是在利用社會大眾對旅人故事的著迷。旅人故事這一文學題材於1590年代由理察.哈克呂特首度予以發揮,撒繆爾.珀柯斯於1610和1620年代期間將其化為商品販售,約翰.史畢德則為這一文學題材提供了地圖和插圖。它帶給讀者莫大的樂趣,且一直到18世紀末期柯爾律治在椅子上打盹為止,魅力一直不減。但從新發現之土地傳來的消息,對其他知性範疇也帶來強烈影響。一有那樣的消息送達,約翰.塞爾登之類的學者即竭盡所能挖取能幫助他們瞭解那些地方和傳統的知識,精通諸種語言,並收集為挖掘湮沒不明的更深層人類歷史真相所需的手抄本。 這一新知傳來時,最初什麼都沒改變,世界只是變得更完整。但漸漸的,隨著證明別種生活方式和思惟方式存在的證據更為頻繁的出現,有些人理解到舊方式並非唯一的方式,甚至說不定得予以修正或揚棄。置身約翰.塞爾登的時代,要經歷典範上的這一轉移。有些人(在塞爾登身上尤其明顯)順著這股潮流而動,運用新見解為歐洲人的知識打下更強固的比較基礎。其他人因這些改變而無所作為,不清楚該如何回應當前世界所正在呈現給他們的事物。但還有些人完全被拋到後面,固守舊的看法,且在這些未經檢驗的看法已因站不住腳而垮掉許久以後,仍信持不悔。 就連最優秀、最聰明之人都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陷入不知該重新肯定舊東西、還是吸收新東西的困境。塞爾登的希伯來語、阿拉伯語老師和後來成為塞爾登學界友人的詹姆斯.烏雪轉向古希伯來語文本,而把天地創造的時間斷定為西元前4004 年10 月23 日凌晨。他擁抱新出爐的原始資料,嘗試運用隨著對世界有更多瞭解而誕生的比較方法,但他從那些原始資料汲取知識,只為證實聖經的記述,而非予以挑戰。不久後,下一代的學者就會在東方文本(特別是中文文本)裡找到豐富的證據,證明人類史的年表起於西元前4004 年之前許久。烏雪若更細心注意他的原始資料,少放些注意力在自己的認定上,可能就不致白忙一場,儘管如此一來,他大概會沒沒無聞於今日。全球性的知識增長,使某些思想家撬開歐洲思想的意識形態樓板,而聖經的開天闢地說只是這一知識增長的受害者之一罷了。為何聰明之人學起希伯來語、阿拉伯語,乃至中國話,原因在此。這些古老語言裡藏有重要資訊;密碼得以破解。東方學者是他們那一代的駭客。 塞爾登或許把他的「中國地圖」視為世界另一頭有先進知識的明證。但他認為這張地圖是有密碼需要破解的文獻嗎?這地圖裡有著他非搞懂不可的東西嗎?他從未就這張地圖表示過看法,因此我們無從得知。但我仍不由得推測他表示過看法,推測他在這張亞洲另一頭的地圖裡,察覺到值得學習且是他原本推斷不出的東西。 對於這一說法,我所能提出的最有力的支持證據,乃是《榮譽稱號》(Titles of Honor)裡的一個段落。這本書是塞爾登備受肯定的專題論著,也是在他因《什一稅史》惹上麻煩之前的第一本重要的學術著作,探討貴族階級與特權的歷史。這個段落不在該書的1614 年初版中,而在他替1631 年再版所添加的獻詞中。他在此獻詞中論道,「所有島嶼和大陸(大陸其實只是較大的島)如此分布,因而不管從哪個島嶼或大陸出海,都必然會發現別的島嶼或大陸。」島與島間會有輕易的交通往來:這不是什麼高深的見解。但歐洲人的經驗會自然而然催生出這個看法嗎?仔細瞧瞧歐陸地圖,沒什麼東西能使人產生這種看法。沒錯,在歐洲邊陲有一些(大不列顛)島嶼,但這些島嶼長久以來反抗從別的陸地過來者。再仔細瞧瞧塞爾登地圖,眼光不自覺地就盯在那些星羅棋布的島嶼、半島和較小的大陸上,而它們的確「如此分布」,致使其中沒有哪個能與別個不相往來。 提出這一看法後,塞爾登接著思考了可從它順勢推出的兩個論點。第一個是「有人把這當成『大自然的邀請』,邀人從一地移居到另一地」。這一觀點實質上在重述發現無人居的異地有權予以占領的無主之地論。第二個推論,且是較侵略性的推論,乃是「另有一些人強調它,好似相互通商的公共權利是它所設計的」。在此,我們與德赫羅特的自然法觀點正面相遇。那一觀點認為商業交易是自然本有的,因而是合法的,凡是阻礙那交易者,都可合法予以挑戰。我們知道塞爾登對這兩個主張都心存懷疑。他認為,只有在其他條件都符合時,才可搬出占地權利和通商權利,而那些條件之一是對等:一方不能將踐踏較基本權利的貿易條件或不平等合同強加在另一方身上。 塞爾登並非為了壓下德赫羅特的氣勢而在《榮譽稱號》中插入這一看法。事實上,他運用島與島間往來相通這個意象時,純粹把那當成暗喻,藉以闡明另一個觀點,亦即令人遺憾的,許多「有用的技藝與學問」領域已各走各的,不相往來,然而「那每個領域都與別的領域關係密切,不只常借助於相鄰的領域,而且透過那層借助,還借助該領域之外的東西」。用今日的措詞來說,每個學科都利用其他所有學科,都與其他所有學科有某種關聯,不該各搞各的,涇渭分明。那純粹是個暗喻,但看過這張地圖之後,我不由得注意到他所選擇之意象和那時他大概已擁有的這張地圖之間的相似之處。很難想像塞爾登是在定睛細瞧歐洲地圖時,想出這一闡明跨學科學習之必要性的意象。但若說他是在看他的東亞地圖時得出這意象,那就一點也不牽強。 沒錯,上述說法出於我的猜測。我如此猜測,乃是因為知道塞爾登看重這張地圖,才會在他的遺囑裡具體交代它未來的歸屬,而他對這樣一張地圖不可能毫無所感。這張地圖於他有何意義?他從未表明。但我們不必因此就閉口不談。如果他不願意向我們透露他如何判讀這張地圖,我們就自己去把它找出來。 初見這張地圖時,我覺得它像個有待完成的拼圖,如今亦然。拼好的區塊愈大,它愈是讓人困惑。對此,我並不驚愕。所有地圖都是拼圖,都被根據它們所處時代的傳統作法和製圖者一時的想法加了密碼。欲判讀古地圖,就得弄清楚它的密碼,並忽視我們自己的部分密碼,以免一時不察,誤把地圖繪製者的手法當成我們今人的手法。我們最不該做的,就是以高高在上的心態看待古地圖。地圖的好壞始終只能以其當初設定的用途來判定,有的比較合用,有的較不合用。地圖繪製者把某個東西畫成某個樣子,因為那就是他要呈現的樣子。如果他當初想畫成另一個樣子,他就會畫成那個樣子。有問題的是我們,不是他。我們覺得某張古地圖「不對」時,那純粹是因為我們未弄懂它的密碼。事實上,「不對」之處可能正是尋找破解密碼線索的最佳切入點。它的密碼和我們的密碼未能吻合之處,正是我們最該仔細檢視之處。 但我得提醒大家:別指望破解所有密碼。塞爾登地圖遍布祕密。其中只有某些祕密會被我們解開。我算過,僅僅六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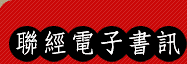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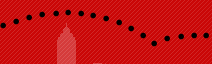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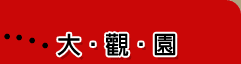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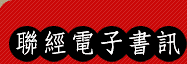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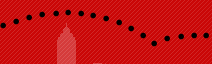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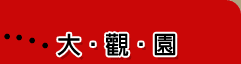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