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鷺號三部曲之二:煙籠河 欲罷不能的葛旭(Amitav Ghosh)《罌粟海》後,
愛不釋卷的史詩之作《煙籠河》登場!
他們各自懷抱不同目的來到謎樣的中國,
卻在煙籠霧罩的珠江口,
身不由己捲入時代的風暴…… ※ ※ ※ 關於阿拿西塔號是否遇上襲擊朱鷺號的同一場暴風雨,後來眾說紛紜,以當時的情報,很難提供可靠答案:但可確定的是,阿拿西塔號在大尼可巴島西方不到一百哩處往尼可巴海峽前進時,也遇上同樣的壞天氣。當時她已離開孟買十六天,正在先去新加坡再轉往廣州的航程中。 直至當時,整趟旅途波瀾不興,阿拿西塔號風帆全開,穿越了幾個航線上的風暴。阿拿西塔號是艘俐落優雅的三桅船,是少數在孟買建造的船隻之一,一般狀況下速度比英美製的鴉片船都快,甚至包括家喻戶曉的紅海盜號與海巫號。這趟航程中,她同樣飛速前進,似乎又將創下另一個紀錄。可是九月的孟加拉灣向來以天候難測而惡名昭彰,當天色突然變暗,不苟言笑的紐西蘭船長一秒都不浪費,立刻停船。當風勢持續增強,他不得不派消息給船主巴蘭吉老爺,建議他到船東套房內小憩,這段期間最好待在裡面別出來。 幾小時後,巴蘭吉仍在船東套房裡,這時船務長維可衝進來,告知貨艙裡的鴉片箱鬆脫散開了。
Kya?維可,這怎麼可能? 是真的,頭家,我們得想想辦法,快點。 巴蘭吉在維可的腳跟後頭匆匆下樓,努力在濕滑的艙室扶梯上站穩,貨艙門的安全設計十分嚴密,搖晃的船身只讓解開鏈鎖變得更加不易。最後,當巴蘭吉總算將一只油燈探進艙門移近地板,發現自己正盯著一個難以理解的場面。 後艙的貨物幾乎全是鴉片,在暴風雨摧殘下,幾百只箱子已鬆脫碎裂,裝鴉片的陶製容器猶如炮彈撞上艙壁,內容物灑得到處都是。 鴉片這會兒成了泥棕色:雖然觸感粗澀,但混入液體時仍會溶解。阿拿西塔號的造船工並非不曾想到這點,因此用盡心思設計能防滲漏的艙壁,可是船身在暴風劇烈晃動下,木板接縫開始「出血」,濕滑的雨水及底艙的海水滲了進來。濕氣讓固定貨物的粗麻繩變脆,這時繩子也已斷裂,貨箱相互碰撞,潑灑出的內容物成了泥漿。臭氣薰天的黏稠液體隨著船身搖晃傾斜,從一側橫掃至另一側,拍打著貨艙牆壁。 巴蘭吉從沒遇過這種情況:他經歷過多次風暴,從未見過託運的鴉片弄得如此七零八落。他自認行事謹慎,而在中國經商三十餘年,他發展出一套獨門鴉片裝箱運送程序。貨艙中的鴉片分為兩類:三分之二是來自西印度,做成小型圓餅,類似某種粗黃糖的「摩臘婆」(Malwa)。這種鴉片在運送過程中不會特別包覆,只用罌粟葉和少許葉莖碎料包起。其餘的則是「孟加拉」鴉片,包裝較嚴密耐久,每塊鴉片餅都小心裝入形狀尺寸像極炮彈的硬殼陶罐中。每箱可裝四十只這種陶球罐,每顆球罐則放在由罌粟葉、稻草和其他收割剩餘碎料堆出的格位中。箱子用芒果木製作,要應付從孟買到廣州約三、四週的航程絕對夠堅固也夠安全:破裂情況極少見,損壞往往是滲水和濕氣造成。為避免這種狀況,巴蘭吉通常會在每排箱子之間預留空間,以保持空氣流通。 這些年來,巴蘭吉這套做法一向是安全保證:在印度與中國間往返穿梭這數十年,一趟航程中他頂多只須報銷一到兩箱貨。過往經驗讓他對自己的做法信心滿滿,於是當阿拿西塔號遇上暴風雨時,他壓根沒想到要巡貨艙,是脫韁的箱子發出的碎裂聲驚動船員後,他們才通報維可。 巴蘭吉低頭查看,只見撞上艙壁的碎裂貨箱猶如在暗礁上撞毀的木筏,貨艙裡到處是撞上龍骨後爆裂的硬殼鴉片球,生鴉片膠凝塊則像碎彈片亂飛。 維可!我們得處理一下,趁箱子全部散開前進去綁好。 維可人高馬大,挺著個滾圓肚皮,有張黑得發亮的臉孔,雙眼外凸,眼神戒慎。他本名叫維多里諾.馬提恩霍.索列斯,是「東印度人」,來自一個距孟買不遠,名叫瓦賽(Vasai)或巴薩因(Bassein)的村莊。他粗通多種語言,其中包括葡萄牙語,大約二十年前開始在巴蘭吉手下工作後,便總是以葡萄牙語的patrão(也就是「頭家」)稱呼巴蘭吉。然而自從維可晉身船務長,他要管理的就不僅是巴蘭吉的私人事務,更兼軍師、中間人與生意夥伴。他還長期投資部分收入在老闆的事業上,這使他再也不是從前那個無足輕重的小角色。他在孟買及其他幾個地方置有產業。身為虔誠天主教徒,他還以母親之名資助一座小教堂。 因此,維可繼續跟著巴蘭吉遠行就不只是為了討生活,還有其他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持續關注自己的投資。他在阿拿西塔號這趟所載的貨上也投入不少資金,對於這批貨的安全,他的關心絲毫不亞於巴蘭吉。 你先在這裡等一下,patrão。他說:我去找幾個船工來幫忙,你可別自己下去。 為什麼? 維可走到一半,轉頭補上一句提醒:要是這艘船發生什麼事,patrão就會自己一個人困在這下面,不是嗎?在這裡等我─我很快回來。 巴蘭吉心知這忠告沒錯,只是在這情況下很難聽進去。他正值壯年,是個停不下腳步的人:休息對他來說如同折磨,他曾有好幾次無法說話或移動時,設法自制的結果通常會變成一場輕點腳尖、彈舌出聲或扳折指關節的小小風暴。現在他倚在艙門邊,嗅到冉冉升起的瀰漫煙霧:那是生鴉片的甜膩氣味融合底艙海水所產生令人頭暈腦脹的窒人臭氣。
要是他還年輕,仍然纖瘦輕盈,身手矯健,絕對二話不說直接爬下梯子,可他如今年近花甲,關節已開始不太靈光,腰圍也明顯寬了不少。不過他只是壯碩,還算不上發福(如果能這麼說的話),容光煥發的氣色和粉嫩臉頰顯示仍舊充滿活力、精神充沛。空等命運之神下決定不是他的風格:他卸下罩袍,開始往下爬進貨艙,卻正巧碰上一陣劇烈晃動,梯子也跟著傾斜搖擺。 他的手臂環著鐵柱,小心緊握油燈把手,儘管如此小心,仍未料到腳下黏稠滑溜的軟泥。板條箱的碎片、包在乾葉片與葉莖碎料中灑出的內容物,現在全與泥漿融為一體。艙底木板像沾滿堆肥的地板一樣濕滑,腳下不管踩到什麼全都裹著一層草莖碎葉,稠得像牛糞似的。 巴蘭吉剛離開階梯,雙腳就驟然一滑,整個人面朝下趴在一堆糞土般的泥濘中。他勉強轉身撐成坐姿,背靠梁柱,這時伸手不見五指,油燈也滅了,不消多久他的衣服便在泥濘中浸得濕透,從頭巾頂到及踝的開襟外衣邊緣全都一樣:鴉片也讓黑色皮鞋內的趾縫間吧唧作響。 有個又冰又濕的東西貼在臉上,他伸手想要抹掉,但說時遲那時快,船身陡斜一晃,那坨濕滑的東西擦過唇邊後反而送進嘴裡。剎那間,在顛簸搖晃的黑暗中,箱子和容器在他身邊滑動碰撞,腦門充滿鴉片令人暈眩的味道。他開始搔抓皮膚,覺得噁心難耐,試著抹掉臉上的膠泥,可是又一個木箱撞上手肘,於是更多鴉片順勢滑入嘴唇。 一縷燈光在上方的艙門走道上閃爍,有個聲音擔心地喊道:patrão?patrão? 維可!我在這裡!巴蘭吉盯著油燈,看著燈光緩緩向他移來,再走下搖晃的梯子。接著船身再次傾斜,這次他被甩到貨艙另一側的泥漿裡,眼睛、耳朵、鼻腔和氣管內全是鴉片─彷彿溺水一般,當下許多面孔從眼前一閃而逝─人在孟買的妻子詩凌白、兩個女兒,幾年前在廣州過世、外號荔枝妹的情婦芝美,以及和她生下的兒子。芝美的面孔在他眼前縈繞不去,他坐起身咳得唾液飛濺時,她的雙眼似乎仍然緊瞅著他,她的存在如此真實,他伸手想要觸碰─卻發現自己望入的是維可的油燈。 他的雙手本能地摸向自己的卡斯堤─那條七十二針的腰布,這是他信仰的聖物,總會圍在腰間。自孩提時代起,這條卡斯堤就是他的護身符,保護他不受不可知的威脅─但一摸到腰布,他馬上就發現腰布也在泥濘中浸濕了。 緊接著,除了頭頂的暴風咆哮聲,他還聽見碎裂崩垮聲,彷彿這艘船就要四分五裂。船身陡然傾向右舷,維可和巴蘭吉在貨艙地板上滑倒,當兩人癱坐在地板和舷牆間的夾角,散落的鴉片球如炮彈砸在木板上。每一顆球都值不少銀子─但此刻巴蘭吉和維可沒這心思去想它的價值,阿拿西塔號的船身如此陡斜,幾乎可以肯定這船就要翻覆。 不過這時,船身開始以十分緩慢的節奏停止擺盪,龍骨的重量將船身從傾覆邊緣拉回。當船身回正,她先晃向另一側,再擺盪回去,就這樣回復了不甚穩定的平衡。 維可的油燈奇蹟似的還亮著,船身傾斜漸緩後,維可轉向巴蘭吉:patrão?發生什麼事了?你怎麼這樣看著我?你看見什麼了? 巴蘭吉瞥向他的船務長,心頭忽地一震:維可渾身上下,從黑玉般的頭髮頂端直到靴尖全都沾滿棕色泥漿。維可向來謹慎打理外貌,總是穿歐式服裝,這模樣著實怵目驚心:如今他的襯衫、背心和馬褲厚厚覆著一層鴉片,幾乎像是滲進表皮底下。他炯炯發亮的大眼頓時與滴著泥漿的暗黑面孔形成強烈對比。 你在說什麼,維可? patrão剛才伸出手的時候,好像撞了鬼一樣。 巴蘭吉唐突地搖頭:Kai nai─沒什麼。 可是patrão─你還喊了一個名字。 福瑞迪? 是的,可是你叫的是他另一個名字─他的中國名字…… 阿發? 巴蘭吉幾乎從不用這名字,維可十分清楚:不可能─你一定聽錯了。 沒有錯,patrão,我跟你說,我真的聽見你這麼喊。 巴蘭吉腦袋一片混濁渾沌,舌頭似乎變得肥厚,他開始喃喃自語:一定是那味道……這些鴉片……我看見東西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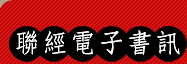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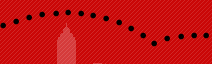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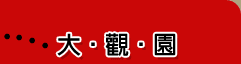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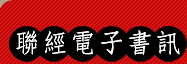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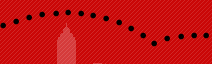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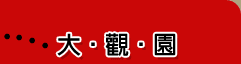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