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之血(歐康納驚世代表作,台灣首度中譯) 1.
海索•莫茲以前傾之姿坐在綠絨布火車座椅上,這一分鐘望著窗外,一副可能要跳出去的樣子,下一分鐘又望向車廂另一頭的走道。火車正迅速穿過不時分開的樹頂,露出矗立在最遠處樹林邊緣的太陽,非常的紅。更近些的地方,犁過的田畫出弧線然後消逝,還有幾隻肉豬用鼻子頂著犁溝,看起來像是長了斑點的大石頭。坐在這節車廂,就在莫茲對面的瓦莉•蜜蜂•希奇卡克太太說,她認為這樣的向晚時分是一天中最美的時刻,她還問他是不是也這麼想。她是個胖女人,領口跟袖口都是粉紅色,還有一雙從火車座椅上斜斜伸出卻碰不到地板的梨形雙腿。
他看了她一秒,沒有答話,接著身體就往前靠,再次瞪著車廂另一頭。她轉頭去看後面那裡有什麼,但看到的只有一個孩子在其中一個位子上四處張望,而在更遠的車廂末尾,有個車廂服務員打開了收床單的櫃子。
「我猜你是要回家。」她又轉回他這邊說道。在她看來,他沒超過二十歲太多,不過他腿上有頂硬梆梆的黑色寬邊帽,是鄉下老傳教士才會戴的帽子。他的西裝是扎眼的藍色,價格標籤還釘在衣袖上。
他沒有回答或把視線從正在看的不管什麼東西上移開。他腳邊的袋子是個軍用旅行袋,她認定他曾經當過兵又退役,現在正要回鄉。她想靠近以便看見那套西裝花了他多少錢,但發現自己反而瞇起眼看他的雙眼,幾乎像是要望進那雙眼睛裡面。那雙眼睛是胡桃殼色,深陷在眼窩中。他皮膚底下的頭骨形狀十分平坦而引人注目。
她覺得厭煩了,便硬是轉移注意力,瞇眼去看那價格標籤。這套西裝花了他十一塊九毛八。她覺得這就能看出他的身分地位,於是再次注視他的臉,好像她現在針對那張臉加強了防禦。他有個伯勞鳥喙般的鼻子,兩邊嘴角各有一條長長的水平皺紋;他的頭髮看似被那頂沉重的帽子固定成扁平狀,不過她注意得最久的,還是他的眼睛。那雙眼睛如此深陷,在她看來幾乎像是通往某處的通道,而她往前靠,越過分隔兩張座位的一半空間,設法要望進那雙眼裡。他突然間轉向窗口,然後幾乎同樣迅速再轉回原本凝望的地方。
他在看的是那個車廂服務員。他剛上車時,那服務員站在兩節車廂之間——一個體格厚實的男人,有顆渾圓的黃棕色光頭。海茲停下腳步,服務員目轉向他又飄開,指出他要去的是哪個車廂。但他沒有移動,服務員便說:「往左走,」口氣很急躁:「往左走。」海茲就走了過去。
「唔,」希奇卡克太太說:「沒有任何地方比得上家。」
他瞥了她一眼,看出她的臉很平坦,在一頭帽子似狐狸的紅棕色頭髮下顯得泛紅。她是在前兩站上車。在此之前他從未見過她。他說道:「我得去找那個服務員。」。他起身,走向車廂末端,那服務員已開始在那裡鋪起臥鋪。他在服務員身邊停下,靠著一個座位扶手,但服務員沒有看他。他正把一塊車廂隔板往外拉長些。
「你鋪好一個鋪位要多少時間?」
「七分鐘。」服務員這麼說,看都沒看他。
海茲坐在座椅扶手上。他說:「我從伊斯卓德來的。」
「那地方不在這條線上,」服務員說:「你上錯車了。」
「我要進城,」海茲說:「我說,我是在伊斯卓德長大的。」
服務員什麼都沒說。
「伊斯卓德。」海茲說道,這次又大聲些。
服務員把遮陽罩扯下。「你要我現在就把你的鋪位鋪好,還是你站在那裡是想要別的東西?」
「伊斯卓德,」海茲說:「靠近梅爾西。」
服務員把座椅的一邊扳平。「我是芝加哥來的,」他說著,把座椅另一邊也扳下來。他彎腰時,頸背鼓起三個凸塊。
「是啊,我猜你是。」海茲斜乜著眼說。
「你的腳踩在通道中央。會有人想從你旁邊過。」服務員說著,突然轉身擠過去。
海茲起身,在那裡停了幾秒。他看起來像是被一條綁在背部中央,然後連到車廂天花板的繩子給制住。他注視著服務員踏著踉蹌但控制得宜的步伐沿著通道走去,消失在車廂彼端。他知道這服務員是個姓巴倫的黑鬼,來自伊斯卓德。他回到自己的座位,弓起身子,低頭縮肩,一隻腳擺在從窗底通過的一條管子上。伊斯卓德填滿他的腦海,然後再往外延伸,填滿了從火車延伸出去,越過漸暗空曠田野的空間。他看到兩棟房子,鐵鏽色的道路和幾間黑人住的棚屋,那間穀倉,還有側邊貼著剝落的紅白兩色CCC嗅劑廣告的畜欄。
「你這是要回家嗎?」希奇卡克太太問道。
他不悅地望著她,同時抓住那頂黑帽的帽沿。「不,不是。」他用尖銳高亢、帶鼻音的田納西口音說道。
希奇卡克太太說她也不是。她告訴他,她結婚前曾是氣象預報小姐,她要去佛羅里達拜訪已經結婚的女兒莎拉•露西兒。她似乎是說她自己從來沒時間到那麼遠的地方旅行。而世事就是這樣,一件接著另一件發生,時間好像過得飛快,快到你分不出自己還年輕或是已經老了。
他想,要是她問起,他可以跟她說她是老了。過了一會兒,他不再聽她說什麼。服務員重回這段通道,沒再看他。希奇卡克太太忘了自己原本在說什麼。「我猜你正要去拜訪某個人?」她問道。
「去托金罕,」他說道,然後用力往椅子上擠,注視窗外。「我在那裡誰都不認識,但我要去辦些事。」
「我要去做些以前從沒做過的事。」他說著,對她斜眼一瞥,然後微微彎起嘴角。
她說她認識一個托金罕來的艾伯特•史帕克斯。她說那是她妯娌的連襟而且他……
「我不是托金罕來的,」他說:「我說我要去那裡,就這樣。」希奇卡克太太又開口說話,不過他打斷她,然後說:「那個服務員跟我在同一個地方長大的,但他說自己是芝加哥人。」
希奇卡克太太說她認識一個人,住在芝……
「妳去這裡或那裡都一樣,」他說:「我只知道這樣。」
希奇卡克太太說,嗯,時光飛逝啊。她說自己五年沒見到親妹妹的孩子了,要是見到他們,不曉得自己還認不認得出來。他們一共三個,洛伊、巴伯跟約翰•衛斯理。約翰•衛斯理六歲大,他曾經寫過一封信給她,親愛的媽媽娃娃。他們叫她媽媽娃娃,叫她丈夫爸爸娃娃……
「我猜想妳認為自己得到救贖了。」他說道。
希奇卡克太太抓住她的衣領。
「我猜想妳認為自己得到救贖了。」他重複道。
她臉紅了。片刻過後她說是的,生活本身就很激勵人心,然後她說肚子餓了,問他想不想去餐車用餐。他戴上那頂惹眼的黑帽,跟著她離開車廂。
餐車坐滿了,眾人正等著入座。他跟希奇卡克太太站著排了半小時的隊,在狹窄的通道上搖晃,每隔幾分鐘就平貼著車廂側邊讓一小批人魚貫穿過。希奇卡克太太在跟她旁邊的女人說話。海索•莫茲望著牆面。希奇卡克太太對那女人說起她妹夫的事,他在阿拉巴馬州圖拉佛斯的市立供水廠工作,那位女士則講起一位得了喉癌的表親。最後他們幾乎排到餐車門口,可以看到車廂內的狀況。有個服務生招呼客人到不同地方,遞出菜單。他是個一頭油膩黑髮的白人,他的西裝也同樣油膩漆黑。他像隻烏鴉,從一張桌子衝向另一張桌子。他打手勢招來兩個人,隊伍前進了些,所以海茲、希奇卡克太太還有跟她聊天的那位女士都準備好下一批入座。過了一分鐘,又有兩人離開。服務生招招手,希奇卡克太太跟那女人走了進去,海茲跟在她們後面。那男人制止他說:「只有兩位。」然後把他推回門口。
海茲的臉變成醜陋的紅色。他設法要走到下一個人後面,然後又試著穿過人龍回到原本的車廂,但是入口處擠了太多人。他只得站在那裡,旁邊每個人都在看他。有一陣子都沒人離開。最後,餐車另一頭有個女人站了起來,服務生的手抽了一下。海茲猶豫了,然後看到那隻手又抽動一下。他腳步蹣跚地走過通道,一路上跌撞到兩張桌子,他的手因此被某個人的咖啡弄濕。服務生把他安置在三個外表年輕,穿得像鸚鵡的女人身邊。
她們的手放在桌面上,指尖像紅色的矛。他坐下,在桌布上擦手。他沒有拿掉帽子。這幾個女人已經吃完,正在抽菸。當他坐下時,她們停止交談。他指向菜單上的第一道菜,站著俯瞰他的服務生說:「年輕人,寫下來。」然後對其中一個女人眨眨眼;她用鼻子發出某種雜音。他寫下菜名,服務生拿著走開。他坐著,陰沉專注地注視對面那女人的脖子。偶爾她拿菸的手會經過脖子上的斑點;那隻手會離開他的視線,然後再度經過,再回到桌面;下一秒就有一道筆直的煙吹向他的臉。在煙朝他臉上吹了三、四次後,他注視著她。她臉上有種母鬥雞肆無忌憚的表情,那雙小眼直盯著他。
「要是妳能得到救贖,」他說:「那我就不想要了。」然後他把腦袋轉向窗口。他看到自己蒼白的倒影,映襯在從窗戶透進的黑暗空曠空間之上。一輛貨運火車呼嘯而過,把空曠的空間切成兩段,其中一個女人笑出聲來。
「妳以為我相信耶穌嗎?」他說著靠向她,講話時幾乎像是喘不過氣。「嗯,就算祂存在我甚至也不會信。就算祂就在這輛火車上也一樣。」
「誰說你非信不可?」她用有毒似的東部口音問道。
他退了回去。
侍者為他上晚餐。他開始吃,起初速度緩慢,後來那些女人專注地看他咀嚼時下巴挺出的肌肉,他就吃得快些。他吃的是某種灑上蛋跟肝臟的東西。他吃完了,喝掉咖啡,然後抽出錢來。服務生看到他,但沒來結帳。每次他經過餐桌,就會對這群女士眨眼,然後瞪著海茲看。希奇卡克太太跟那位女士已經吃完離開。終於那男人過來,結了帳單。海茲把錢推給他,接著便擠過他身邊離開車廂。
他在空氣算是新鮮的兩節車廂中間站了一會兒,拿出一支菸。然後那個車廂服務員經過兩節車廂之間。他喊道:「嘿,巴倫!」
車廂服務員沒停下腳步。
海茲跟著他進入車廂。所有鋪位都鋪好了。梅爾西車站的人賣了張臥鋪車票給他,因為他說他在一般旅客車廂得坐著熬一整夜;那人賣給他的是上鋪。海茲來到鋪位,把行李袋拉下來,然後走進男廁,做好過夜前的準備。他吃得太撐,想加快動作,好進臥鋪躺下來。他想著自己會躺在那裡,望著窗外,注視著鄉村如何在黑夜中的火車外掠過。有個標示說,要進上鋪請找車廂服務員。於是他把行李袋往上放進鋪位,然後去找服務員。他在車廂這頭沒找到人,就回到另一頭。走過轉角時,他撞上某個沉重的粉紅色玩意;它驚喘一聲,低聲吐出一句:「笨手笨腳的!」那是穿著粉紅浴衣的希奇卡克太太,她的頭髮打成小結,掛在腦袋周圍。她望著他,眼睛瞇到近乎閉起來。那些小瘤框著她的臉,看起來像黑色毒蕈。她設法要走過他身邊,他也想辦法讓她通過,但兩人每次卻都移往同一邊。她的臉上除了一些白色小斑塊之外,已脹成了紫色。她身子一僵,停止動作說:「你怎麼回事啊?」他溜過她身邊,衝進走道,結果撞上那服務員,把他撞倒了。
「巴倫,你得讓我進臥鋪。」他說。
服務員自己爬起來,面無表情,搖搖晃晃沿著通道走開,一分鐘後又搖搖晃晃地回來,這次帶著梯子。海茲站在那兒注視他把梯子搭上;接著海茲開始往上爬。爬到一半時,他轉身說:「我記得你。你父親是個黑鬼,叫凱許•巴倫。你不能再回那裡,所有人都回不去了,就算他們想回去都不行。」
「我是芝加哥來的,」服務員用惱怒的聲音說:「我不姓巴倫。」
「凱許死了,」海茲說:「他得了霍亂,他被豬傳染了霍亂。」
車廂服務員的嘴往下一撇,然後說:「我父親是個鐵路職員。」
海茲笑出聲來。那服務員突然手臂一抽把梯子拿走,把這緊抓著毯子的男孩送進鋪位。他在那裡趴了幾分鐘,動都沒動。過了一會兒,他轉身發現燈光,同時環顧四周。這裡沒有窗戶。他被關在這玩意裡面,只有窗簾上方有一點點空間。鋪位天花板很低,而且呈弧形彎曲。他躺下來,注意到彎曲的天花板看起來不像完全封閉,而是正在關上。他躺了一會兒,沒有移動。他喉嚨裡有個東西,像一塊帶雞蛋味的海綿;他不想翻身,害怕它會移動。他想把燈關掉,沒有翻身就伸出手,摸到開關把燈熄掉,黑暗下沉到他身上,然後消退了一點點,因為從通道上有些微光線從門底那點未密合的空間透入。他希望這裡一片漆黑,他不想要這片黑被稀釋掉。他聽見服務員的腳步聲沿著通道過來,踩在地毯上,又輕又柔,穩定地朝這走來,掃過綠色窗簾,然後在另一頭逐漸消失在聽力範圍之外。又過了一會兒,在他幾乎要睡著時,以為自己又聽到那腳步聲回來了。他的窗簾抖動一下,腳步聲再次消逝。
半夢半醒間,他覺得自己躺的地方就像個棺材。他所見過第一個裡面躺著人的棺材是他祖父的。裝著老人的棺木在屋內停靈那一夜,他們用一根引火棒撐開棺蓋,海茲從遠處望著,心想:他才不會讓他們把棺材蓋在自己身上;到時他會把手肘猛地撞進縫隙裡。他祖父曾經是個巡迴傳教士,一個像黃蜂般易怒的老人,把耶穌像根針似地藏在腦袋裡,奔波在三郡之間。但等到要將他下葬,他們把那箱子的頂蓋封上時,他動都沒動。
海茲有兩個弟弟;一個嬰兒時就死了,被放進一個小箱子裡。另一個則在七歲的時候摔倒在一台割草機前。裝他的箱子大概只有普通尺寸的一半,他們關上箱子時,海茲跑過去再打開來。他們說他會這麼做,是因為跟弟弟分離而心碎,但不是那樣的;那是因為他本來在想,如果是他在箱子裡,而他們把他關在裡面的話怎麼辦。
他現在睡著了,夢見自己再次出席父親的葬禮。他看到父親弓著身子,四肢著地趴在棺材裡,就這樣被抬去墳場。「如果我一直把屁股撅在半空中,」他聽到老人這麼說:「就沒有人可以拿任何東西把我蓋住。」不過他們抬著他的棺材到墓穴旁,就這麼咚一聲放下,他父親就跟其他人一樣攤平了。火車顛簸搖動,再次把他弄得半醒,而他心想,那時候伊斯卓德一定有二十五個人,其中有三個人姓莫茲。現在再也沒有姓莫茲的人了,再沒有姓艾許菲爾的,沒有姓布萊森甘姆、費伊、傑克森……或者巴倫——連黑鬼都受不了了。他轉向道路,在黑暗中看到門面釘上木板的封閉店鋪、傾斜的穀倉、還有被拖車拖走半邊,前廊不見,客廳也沒地板的的小房子。
他十八歲離開時,那裡不是這樣的。那時候那裡有十個人,而且他沒注意到,那裡從他父親的時代之後,規模就變小了。他十八歲時離開那裡,因為軍方要他入伍。他起初想過要射傷自己的腳來逃避兵役。他會像祖父一樣成為傳教士,而少了隻腳還是能做傳教士。傳道人的力量在於他的脖子、舌頭跟手臂。他祖父開著一輛福特汽車在三個郡間旅行。每個月第四個週六,他會開到伊斯卓德,彷彿剛好及時把他們全都救出地獄似的,在打開車門前就開始大喊大叫。大家會聚在他的福特車旁,因為他剛才似乎在挑釁他們不敢這麼做。他會爬上車頭,就在那裡布道,有時他還會爬到車頂,往下對他們大吼。他們就像石頭!他會這樣吼著。可是耶穌會為救贖他們而死!耶穌對靈魂如此飢渴,祂因此而死,衪為所有人而死,他會為一個人而承受每一個靈魂的死亡!他們懂這個嗎?他們瞭解嗎,為了每個頑石般的靈魂,他會死一千萬次,為了他們當中的某一個人,而讓自己的手臂跟腿在十字架上展開,被釘上一千萬次?(老人這時會指向孫子海索。他對海索有種特別的輕蔑,因為他的臉幾乎一個模子刻出來似的重現在這孩子臉上,猶如在嘲弄他。)他們可知,就算為了那邊那個男孩,為了站在那裡那個惡毒、有罪、沒腦的男孩,一雙髒手掛在身子兩邊,一下抓緊一下放鬆的男孩,耶穌會在他輸掉自己的靈魂以前,就讓自己死上一千萬次?祂會追著他跨過罪惡之海!他們懷疑過耶穌能不能走在罪惡之海上嗎?那男孩被拯救了,而且耶穌永遠不會離棄他。耶穌永遠不會讓他忘記自己受到救贖。罪人自以為能得到什麼?耶穌終究會擁有他!
但男孩不必聽這些。他心中早有一種深沉、陰鬱而無言的確信,就是要像逃避罪惡一樣逃避耶穌。他在十二歲時就知道,自己將要成為傳教士。後來他看見耶穌在他內心深處的樹林間移動,一個狂野的衣衫襤褸人影對他招手,要他過去,來到不確定該把腳放在哪裡的黑暗中,在那裡,他可能會走在水上卻不自知,等到突然明白時突然落水溺斃。他想待的地方是伊斯卓德,在那裡他能睜著雙眼,雙手始終觸摸熟悉的事物,雙腳踏在已知的路徑上,舌頭也就不會不受控制。當他十八歲時,軍方徵召了他,他把戰爭看作引領他走向誘惑的詭計,若非堅信自己幾個月後就會回來,好端端地不受腐化,那麼他就要射傷自己的腳。他對自己身上抗拒邪惡的力量帶有強烈信心:那就像他的臉,是某種從祖父身上遺傳來的東西。他心想,如果四個月內政府不放過他,他無論如何也會自己離開。他十八歲時想過,他會給他們不多不少四個月時間。結果他一去就是四年;期間未曾返鄉,連路過探望都沒有。
他從伊斯卓德隨身帶進軍中的唯一一批東西,就只有一本黑色的聖經和一副母親的銀邊眼鏡。他上過一所鄉下學校,在那裡學習讀寫,不過看來,不去上學是比較明智的決定;聖經是他唯一會讀的書。他不常讀聖經,但閱讀時總是戴上母親的眼鏡。但那副眼鏡讓他雙眼疲勞,因此每次短暫讀上一會兒,他就不得不停止閱讀。他本來打算告訴軍中任何邀他犯下道德之罪的人,他來自田納西州的伊斯卓德,他打算回到那裡、留在那地方,他會成為福音傳教士,他不打算讓政府或任何他被派駐的外地害他的靈魂沉淪。
在營裡度過幾週後,他交了些朋友——他們其實不算朋友,但他得和他們共同生活——這時他得到了一直在等待的機會:罪惡的邀約。他把母親的眼鏡拿出口袋,戴了起來,然後告訴他們,就算給他一百萬再加一張可以躺在上面的羽毛軟床,他也不會跟他們去。他說他來自田納西州的伊斯卓德,他不會讓政府或任何被派駐的外地害他靈魂沉……不過他的聲音破了,沒法把這句話講完。他只能瞪著他們,設法板起面孔。他的朋友告訴他:除了神父,沒有人對他天殺的靈魂有興趣,他則設法回答,沒有一個神父會聽命於打算損害他靈魂的教宗。他們告訴他,他沒有任何靈魂,接著就出發前往他們的妓院。
他花了很長的時間相信他們的話,只因為他想相信。他想要的就是相信他們,然後一勞永逸擺脫「它」,他看出自己在這裡有機會擺脫「它」而不受腐化,改宗成為什麼都不信的人,而不是皈依邪惡。軍隊派他繞過半個世界時遺忘了他,當他受了傷,他們又會記得他一下子,但那時間連把砲彈破片從他胸口拿出來都不夠——他們說拿出來了,卻從沒讓他看過那破片,以致他覺得破片還留在那裡生鏽並毒害他——然後他們將他送去另一個沙漠,再次將他遺忘。他有的是時間研究自己的靈魂,並向自己保證靈魂不在那裡。而在他徹底確信這件事之後,他終於明白,其實自己從始至終早就知道這件事。他承受的苦難是對家的渴望;這跟耶穌沒有關係。當軍隊終於放他離開,他愉快地想著自己終究沒有被腐化。黑皮聖經跟母親的眼鏡仍在那個旅行袋底。他現在不讀任何書了,但仍留著聖經,因為那是從家裡帶出來的。他還留著眼鏡,以防將來視力退化。
兩天前,軍隊在他的目的地北方三百哩一個城鎮讓他離開,他立刻前往當地的火車站,買了張到梅爾西的車票,那是離伊斯卓德最近的車站。接下來,既然還得等好幾個小時才能搭車,他就走進車站附近一家陰暗的成衣店。那是個飄著淡淡硬紙板味的店鋪,越往內走越陰暗。他走進店鋪深處,店家賣了件藍色西裝外套和一頂黑帽子給他。他把軍裝放進一個紙袋,然後塞進角落一個垃圾桶裡。當他走到戶外的陽光下,新西裝立刻變成扎眼的藍色,帽子的線條也似乎僵硬得要命。
下午五點,他到了梅爾西,接著搭上便車,一輛棉花籽卡車載著他走過往伊斯卓德的大半路程。剩下的路他用走的,晚上九點時到了那裡,那時天色剛開始變黑。那屋子也像夜一樣黑,而且向著夜晚敞開,雖然看到屋子四周的圍牆已經半塌,前廊地板中間長出了野草,卻未立刻明白這只是個空殼,已經什麼都沒有,只剩房子的骨骸了。他把一個信封扭成長條,用火柴點燃,把樓上樓下,所有空房間都巡了一遍。信封燒完後,他再點燃另一個信封,又全部再巡一次。那天晚上他睡在廚房地板上,有塊木板從屋頂掉到他頭上,割傷了他的臉。
屋裡什麼都沒有,只剩下廚房裡的衣櫥。他母親總是睡在廚房裡,便把她的胡桃木衣櫥擺在那裡。她花了三十塊買這衣櫥,此後沒再為自己買過任何貴重物品。然而不管是誰拿走屋裡其他一切,都留下了這個衣櫥。他打開衣櫥的所有抽屜。最上方的抽屜裡有兩條包裝帶,其他抽屜則什麼都沒有。他很訝異竟然沒有任何人來偷這樣一個衣櫥。他拿起包裝帶,繞在衣櫥腳上綁起來,再穿過地板縫,然後在每個抽屜留下一張紙,寫著:這個衣除屬於海索•莫茲。不要偷,否則你會被找到然後殺掉。
他在半睡半醒間想著那衣櫥,認定若是母親知道有人守護著它,她在墳墓裡會歇息得安穩一些。只要她在晚上來看看就能看到。他納悶地想,她有沒有在晚上來過這裡,臉上仍帶著不得安寧、睜眼直視的表情;他曾透過她的棺木縫隙看到同樣的表情。他們把棺蓋在她身上閤起時,他透過縫隙看到了她的臉。那時他十六歲。他見過那片籠罩在她臉上,把她的嘴角往下拉的陰影,彷彿就算死了她也不覺得比活著滿足,好像她就要一躍而起,把棺蓋往後推開並飛出來才滿意:但他們封上了棺蓋。她本來有可能飛出來,她本來可能會跳出來的。他在睡夢中看見她,很恐怖,像隻龐大的蝙蝠衝出封閉角落,飛了出來,但每次棺蓋都在她上方留下陰影,每一次最後都關了起來。他從棺木裡看到棺蓋關上,越來越近、越來越近地蓋下來,切斷了燈光與空間。他睜開眼,看到棺蓋關上,於是在縫隙間彈坐起來,他的頭跟肩膀立刻卡住,懸在那裡,只覺頭暈目眩,同時車上的微光緩緩映照出底下的地毯。他坐在與窗簾頂端齊高的臥鋪,看著車廂另一頭的服務員,那是黑暗中的一個白色人形,站在原地注視著他,一動也不動。
「我不舒服,」他喊道:「我不能關在這玩意裡面。把我弄出去。」
服務員站在那兒凝視著他,紋風不動。
「耶穌,」海茲說:「耶穌啊。」
服務員沒有動作。「耶穌很久以前就離開了。」他用刻薄的勝利口吻說道。 * * *
直到第二天晚上六點他才到達那城市。因為那天早上他在一個聯軌站下了火車,去呼吸點新鮮空氣,就在他看著另一個方向時,火車溜走了。他追著火車,但帽子又被吹跑,於是他得往另一個方向跑去搶救帽子。幸運的是,他隨身帶著行李來到車外,免得有人從裡面偷走什麼。而他得在聯軌站再等六小時,才有路線正確的火車到站。
抵達托金罕時,他一下火車,就看到招牌跟燈光。花生、西聯匯款、阿傑克斯清潔用品、計程車、旅館、糖果。大多數都通了電,正上下移動或瘋狂閃爍。他走得非常緩慢,把行李袋掛在脖子上。他的頭轉向一邊,然後又是另一邊,先朝向一個招牌,然後再向著另一個。他沿著車站一邊從頭走到尾,接著再往回走,彷彿他可能再搭上另一班火車似的。在那頂沉重的帽子底下,他的臉色嚴峻而堅決。沒有一個觀察他的人會知道,他沒地方可去。他在擁擠的候車室裡來回走動了兩、三次,不過他不想坐在那裡的長椅上。他想要去個有隱私的地方。
最後他推開車站一頭的一扇門,那裡有張樸素的黑白標示寫著:男廁。白人用。他進入一個狹長的房間,一邊是一列洗臉盆,另一邊是一排木製隔間。這房間的牆壁一度是明亮歡愉的黃色,但現在比較接近綠色,上面點綴著手寫字跡,還有男女兩性身體部位的各種細節塗鴉。某些隔間有門,而在其中一扇門上,有著一定是用蠟筆寫的大字——歡迎!!!——後面還接上三個驚嘆號,還有某個看似一條蛇的東西。海茲走進了這一間……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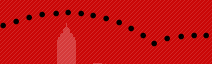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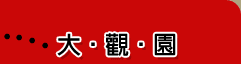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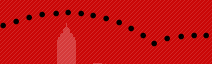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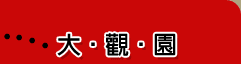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